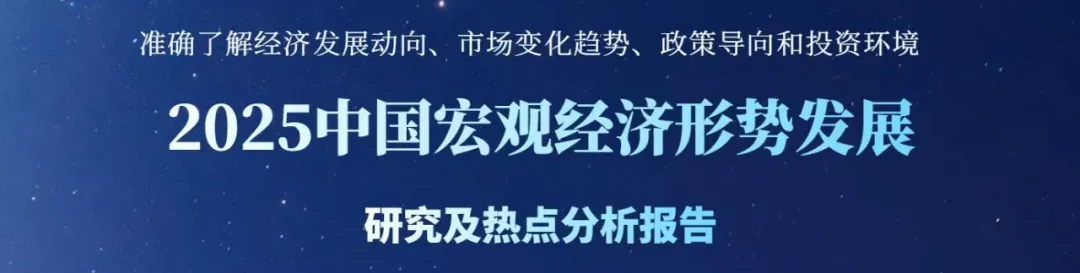对2022年宏观经济的十四点看法
2022-02-05 21:12:46
【导读】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公布2022年经济增速目标,这为观察今年中国经济走势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其中,北京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在5%以上,上海、山东、广东等8地将增速设定在5.5%左右或以上,其余大部分中西部省市将目标设定在6%-7%,海南目标定得最高,为9%。
2020年,在低基数效应影响下,2021年中国GDP同比增速高达8.1%,远超6%的目标。但随着该效应的消退,市场对2022年中国经济的预期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稳增长”目标,余永定认为,在目前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
【文/ 余永定】
第一,我们应该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
2021年中国GDP增速8.1%。如何看待这一经济增速?高于8%的增速是否表明2021年中国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呢?我们可以同疫情前的2019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一下。同比会涉及到基数问题,环比则不直接涉及基数问题。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2019年和2021年各个季度的环比增速。2019年4个季度环比增长速度是1.6%、1.2%、1.3%和1.6%,相应的年化增长速度6.6%、4.9%、5.3%和6.6%。而2021年4个季度的环比的增长速度年化之后几乎都明显(除第四季度)低于2019年。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 2021年的经济是运行在低于2019年6%的水平的。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GDP的增速恐怕就要低于5%。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2021年超过8%的经济增速。
简言之,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任何人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多年来中国经济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
第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处于低通胀甚至是通货收缩状态的。
例如, PPI(生产价格指数)从2012年3月开始连续54个月都是负增长,而直到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们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来说CPI在过去10多年大概不超过2%。2021年下半年物价特别是PPI上涨较快,但最新的数字显示,目前在CPI继续保持低水平的同时,PPI已经开始回落。
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永远不要忘记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至理名言。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
我们当然应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顺便说一下, 提倡“高质量增长”是完全正确的,但100万亿元GDP就是100万亿元GDP。
理论上,在GDP之间不存在质量孰高孰低的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我们必须假定所有GDP是同质的。否则,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的GDP就无法比较了。在产品和项目的层面,确实存在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可能根本不创造价值。如果这些经济活动的产物也被计入了GDP,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监管和统计出了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降低GDP增速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也并不一定要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
第三.我认为,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一个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方法论错误。
我想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不能说这种观点没有一点道理。但“较高”是多高?是10%、8%、7%、6%、还是5%?2010年第一季度12.2%,肯定太高。2019年GDP增速降到了6%、2022年争取实现5.5%,还太高吗?不利的结构性因素充其量能够说明中国GDP增速为什么会有所下降,甚至明显下降,但并不能说明增速到底降到百分之几才是合理的。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没有明确定义。我们习惯上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可以说,“‘结构’是个筐,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从我们经济学家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所谓“结构性”包括: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地位、收入分配不均等、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等。可以说,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的问题,都被同一个词装进去了。
“结构性”问题的单子可以开得非常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在于,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笼而统之的来解释我们某个具体年度、甚至具体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用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是7%、6%、或5%。这种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的思路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
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是12.2%,从那时开始就在下降,几乎是每个季度都要下降。如果从12%降到10%这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接受;那么,从10%降到9%呢?从9%降到8%呢?从8%降到7%呢?从7%降到6%呢?现在又向着5%的方向下降了,是不是还要用同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呢?为什么就不能用某种宏观经济政策来解释呢?
“结构性”的因素肯定是要影响经济增长的,但无法解释经济增速的年度和季度变化,正如你不能用衰老来解释为什么你今天会有血压高、糖尿病。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
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尽管其在几十年中的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但一般而言,在每年、每季度中是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例如,人口老龄化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某个年度或季度经济增速的下降。
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数量庞大,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所谓“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当然,也有特例。如果把“外部冲击”归类于结构性因素,疫情就是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点,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来讲,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难道不能部分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吗?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有什么根据说这种下降一定会使中国GDP增速由2011年的9.6%下降到2012年的7.9%?同理,由人口老龄化推导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低于6%或5%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点,结构性因素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变量,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因果链条,必须找到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才能确认某个结构性因素对某个年度的GDP增速的具体影响。不仅如此,因果链条不是单一、直线的,诸多因果链条还会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直接影响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因素是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等。当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约束时,要分析决定当期供给的供给方因素。结构性因素是通过一个非常长的因果链条,才作用到消费、投资等直接决定GDP增速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如果想证明某特定“结构性”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就需要把因果环节一个个点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用某种量化指标度量的老龄化程度)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最后作用到消费、投资、净出口。要逐一识别这些环节。如果根本没有找到各个环节,就直接跳跃到中国经济增速只能是6%这样的结论,在逻辑上就犯了“假推导”、“推不出”的错误。
宏观经济讨论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
第四,关于刺激消费的问题。
2020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当然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思路。但如果消费者长期固定收入下降、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这时即便发了钱,居民可能也不会花出去,而是会把钱存起来。2020年武汉解封之后,有人认为,消费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种预期并没有实现。直至2021年下半年,消费也没有出现报复性增长。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首先提高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改变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就会比较困难。当然,对于因疫情冲击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必须提供救助,但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第五,如何确定经济增长目标。
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但中国应该争取实现多高的增长速度呢?学界普遍认为,应该首先算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再根据这种计算的结果来决定GDP增长目标。我在过去很长时间也是这种主张。但问题是,模型过于依赖严格的假设,很多基本统计材料阙如,“潜在经济增速”是很难准确计算的。
在我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的职业生涯中碰到过很多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因准确预测了某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趋势而名闻天下。但实际上他们这辈子可能就准了一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计算的、这种计算结果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能以这种计算为依据。
我特别赞成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我也搞不清楚结果会是什么(当然大方向是清楚的),反正咱们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可能不懂经济学,但他们管经济比懂经济学的人管得好。尽管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依然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量世界排名18,GDP低于荷兰那样的“蕞尔小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GDP不足日本的1/4,2010年赶上日本,现在是日本的3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了就是好的。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社会科学院的,进去的第一天就听同事讲中国“货币超发”、要发生通货膨胀、要发生经济危机。大量“超发”的货币是“笼中老虎”,“老虎要出来吃人了”等等。我等 “笼中老虎”出来,等了40多年,头发都等白了。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像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所希望的那样,小心翼翼,不敢冒险,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了。经济学不是一种确定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幸好当初政府没听经济学家的一些中规中矩的意见。如果听了,中国经济增速估计就没有后来保持了近40年的平均10%的经济增速了。
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写了不少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现在再去读那些旧报告就会发现,这些报告的预测大多同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相差甚远,有的可能还是“南辕北辙”。撰写报告的世行专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世界太复杂、中国太复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太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
第六,我以为,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
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如果通货膨胀并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并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
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张。正如我一再强调的,6%具有象征性意义。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为什么不能尝试实现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速呢?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中国必须让经济增速一步步降下来是错误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的“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长期、持续下滑,就会出现以后想快也快不起来了的结果(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就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其结果与其说是经济增速不得不下降,不如说你认为它必然要下降,于是它就下降了。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的过于高了。年年都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单从2008年之后就可以列出一张长单。2012年春节之前,我随北大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拖垮,还有“影子银行”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地下金融的规模和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部分人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第七,增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地缘政治问题。
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上升,我们在下降,增速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无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是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是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的。
第八,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为2022年经济增长确定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公开设定目标?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
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制定明确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去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给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给定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实现的增速。
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同比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后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随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在以往,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直是逆周期变化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能拖累GDP增速呢?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完全不是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它绝不仅限于“铁公机”这样的老基建,而是还包含着“新基建”以及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死亡失踪380人(郑州市)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正视既有问题、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与败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无异于自废武功。
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将拖累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且难于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中国货币当局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方面,希望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有房价调控政策出台,货币当局就会相应退出原来执行的政策。另一方面,房价或房价增速下降则会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并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增速的下降——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国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抑制房价不应该是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仅仅是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也要避免突然改变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
2008-09年四万亿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至于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度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可能就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中国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以且应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即便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并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如果国债市场对国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美国的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
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但是也有必要强调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到底足不足?如果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将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由于中央已经提出“稳增长”的大政方针,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本文为余永定教授撰写的“关于2022年宏观经济的十四点看法”,原载于微信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特别提示:凡注明“来源”或“转自”的内容均自于互联网,属第三方汇集推荐平台,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分享的内容仅供读者学习参考,不代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网的观点和立场。中国经济形势报告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侵权请联系QQ:3187884295进行反馈。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
2.本站的原创文章,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不尊重原创的行为本站或将追究责任;
最新新闻
热点文章